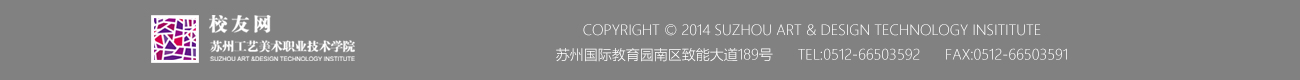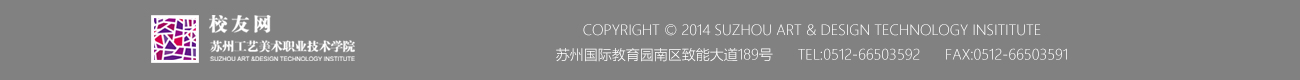出生:1962年
毕业:1983年
专业:工艺绘画
经历:1983年—1986年任教于东山碧螺春书画院
1986年—1988年任教于苏州陆幕中学
1988年—1994年苏州吴县工艺美术公司下属企业
现职:东吴美而高服饰品有限公司董事长,江苏省苏州市花鸟画研究会秘书长、苏州市收藏家协会副主席
华彬(以下简称华):你是老美校毕业的,是比我更早的校友,所以有一些比较感兴趣的问题想问问你。
吴中培(以下简称吴):也不算老美校,七九年以后的。
华:你当初报考美校的初衷是什么?
吴:我报考美校是比较偶然的。我是农村的,就长在太湖边上,在胥口下去叫香山那个地方,现在变成一个书画之乡了,慢慢作为一种产业在画了。那时正好苏州来了一个师傅,就是教下面那一帮人画画,所以我有机会接触到了画画,才十五六岁就开始拿毛笔画国画。到八零年前,我听朋友介绍说苏州美校要招生,他说你在社会上画不出什么名堂,还是要考学校,通过专业培训,那时候离考学校的时候也只有差不多半年不到了。考学校要考素描、色彩,那时候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素描色彩,只是跟着庄上拜师,就是画国画一类的东西。
华:就是传统的那一路的,不是为了考学校准备的。
吴:只是社会上画画。我马上找素描、色彩老师练。那时候还要考语文、政治跟英语,那几个月里很认真很辛苦。
华:拙政园那个老美校,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老师是谁?或者说你个人比较印象深刻的事件是什么?
吴:当时我一进学校一看,好像跟我们以前那种学校完全不一样,亭台楼阁的。完全是苏州园林式的!感觉很不错,环境也好,但是就是教室什么的条件比较艰苦。但是我感觉老师都很认真,对我们在专业上指点都很细心。因为我进学校以前也主要是画花鸟的。那时候主要教我们的是蒋凤白老师。在进学校以前我也喜欢画兰花、画竹子,所以我对他感觉特别亲近,特别想学他的东西。他认认真真地教,我们也认认真真在学。而且那时候不光是一个蒋老师,我看其他老师都是这样,整天就是在课堂里。
华:老一辈的老师都比较严谨、认真。
吴:严谨,而且他备了不少好的东西给我们看,蒋凤白老师就是带着自己的收藏,包括那种名画都拿过来给我们作为临摹。而且他自己在那里示范怎么画,很认真的。所以说那时候我觉得我们学到的东西也不少,而且我感觉我们那时候的学习气氛,因为考进学校也很不容易,基本上都是很刻苦的,而且不是说光上课在画,晚上吃了晚饭就马上上课堂了,基本天天不到九点十点不回去的,那时候最起码到学校关灯我们才回去。那时候是的的确确的认真。一早起来出去画写生画速写。
华:当时在美校差不多一个班十几个同学,那么现在这些同学基本上都还在画画,还是从事各种各样的行业?
吴:据我了解,应该说基本上都在画画。那时候我们班大概有七个还是八个是苏州的。大部分是苏州的。外地一部分也都应该在画画。我联系得到的那几个同学,也都在画画。我们美校出来的那些学生的的确确,不说其他地方,就说在苏州,在画画这方面应该说是影响比较大的。基本上现在苏州这个层面上画的好一点的基本上都是美校毕业的。包括六二届的那些老美校校友,像刘懋善老师、杨明义老师。他们是作为六十年代的那一代,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这一代,应该说都是很优秀的。像徐惠泉,他现在已经是省美协的副主席了。而且他的画现在也在社会上影响很大。
华:中青年这一辈应该说基石是从老美校那边传过来的,大半壁江山。
吴:对,苏州这一块画得好一点的,基本上都是我们美校的。
华:后来怎么会想到要创办这个服饰品企业?自己是有一个初衷还是机缘巧合?
吴:我实际上是从美校毕业以后,本来的愿望是想进画院。但当时一般就是你哪里来回哪里去。本来我是吴县出来的,回吴县的话又没有专业的画院,就想回吴县的工艺公司去。正好那时吴县教育局在东山碧螺春书画院办了一个工艺美术职业班,没老师,硬把我拖到教育局去报到,然后到东山去教书。我就在东山教了三年书。当时是我一个人带专业,外面聘请了一些老师教素描、文化、其他课程。三年下来我觉得我对这个班级的贡献蛮大的,二十八个学生中考取大中专的,有南艺、南师、镇江师专,都是大专以上的,考取了十一个。
华:占一半了。
吴:就是二十八个学生里面出去了十一个,像张美根、蒋金林等等,很多现在在社会上很知名。苏州也有几个现在在画的。办完这个班以后,因为我那时在苏州结婚了,这个班是八六年毕业,我就八五年年底结婚的,在东山就比较不方便,我就要求往苏州调,把我调到陆慕中学去当美术老师。两年后又调回到工艺公司下面的一个企业。本来我是想去搞设计的,但是进去以后他们又缺少跑业务的人,我就开始跑业务了。从开始第一年跑业务,到第二年下半年我就当了业务科副科长,到第二年年底半年不到我就当科长了,三年以后慢慢当副厂长,当厂长了。
华:也不是说自己原来想到?
吴:没想到我会去跑业务,最后做成厂长。但是为什么能这么快适应业务方面,而且人际关系搞得这么好,一下子能从业务员当科长,当副厂长,当厂长,一直到当厂长就是主持这个厂?主要我感觉通过画画,一个人的观察能力、适应能力很快;而且我们那个行业属于工艺类型的,也是对产品的设计、美观、色彩的研究,跟专业还是很有关系的。所以说我有时候出去跑业务跟客人谈的时候,他们一听说我是搞美术的,说出来的话讲出来的东西他们都感觉很内行,很愿意跟我合作。而且他们的一些产品我可以提出我很多不同的看法,或者怎么修改;而且我们开发一些新的东西都是比较对路比较快,一下子能适应客人的口味,所以这方面还是很有好处的。
华:就是美校学到的东西还是帮助很大的?
吴:帮助挺大的。还有就是说,真正画画的人的一种性格、脾气、跟人交往的方式,我觉得还是比较大方,不像生意人那样斤斤计较。
华:一般人都会有这种问题,就是说一边要管公司的事情,一边要进行花鸟创作,这个肯定会有一定的矛盾,你怎么来平衡这种矛盾?
吴:首先这个要有一个前提,就是为什么我当时从八八年开始进入那个行业以后,就慢慢把画丢掉了,实际上当时也觉得经历不够,我要跑业务。因为人家招我进去,我肯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。当时跑业务我经常出去接触客户,自己画方面没这么多精力了,索性我就把画停下来。没想到一下子停了大概十年多。到了2000年以后企业转制,转制以后我跟人家搞了一个合资,那么我只要能把企业管理这一块理顺了,我自己就能脱开了。
华:听说你还有近代收藏,主要是吴昌硕的书画?
吴:对,收藏实际上在我企业转制以后,2000年左右吧。
华:你收藏是出于什么目的?比如说有人是纯粹喜欢,有人是为了保值,还有人是为了倒卖,你是出于什么目的呢?
吴:我当时的收藏考虑的目的只是为自己恢复画画着想。出于专业上研究的一些想法,就是我喜欢的几个画家。价格稍微适中的,便宜一点也不是太离谱的,就是看上去好的,拿回家就当观摹这个类型的。
华:这个大概是画画的人都有的通病,就是看到好东西心里就痒。
吴:对,看到好东西就痒痒,我就慢慢从买画开始,实际上买了以后收藏的瘾开始慢慢大起来。慢慢通过一个阶段我就抽调一部分再换另外一部分,以画养画。
华:我们几个朋友也经常讨论一个问题,就是说像苏州这样的一个城市总感觉出不了大家。比如说像傅抱石这一类的画家,即使就是苏州本地的画家他也好像要换一个地方,去浙江或是去北京。然后他的名声和成就才会提高。这样一个现象是挺奇怪的,或者是说什么原因制约苏州本地产生不了这种大家?有没有考虑过这样一类的问题?
答:实际上我感觉像苏州这一块,从历史来讲的话,从明代到清朝,实际上出了很多的大画家。怎么会逐步到了近现代,苏州反而出不了这么多画家了,好像是脉络给断掉了一样。这个有几个原因,一个就是说整个国家的体制有转变了,因为以前画画的时候不是考虑是省会、首都,那个地方就肯定能出大家,而是考虑一个文化氛围浓的地方,肯定是会出一批大家,通过历代文脉的传播。
华:所以导致常熟、太仓这种都能出大家。
吴:都能出大家,都是一路文脉下来的。苏州地区本身那时候是经济比较发达的,离上海都很近,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它会出这么多画家。那么现在反而是作为一个政治体系,然后就是说在北京出得了大画家,在浙江,在南京,要省会城市反而倒是宣传力度大,接触的人多,接触的宣传机构多,接触的领导又多,慢慢这方面就靠政治因素决定了。还有现在信息社会,有些画家就是靠着信息来推出自己,通过很多宣传网络来做大自己、做强自己。但是在这方面苏州还是保持着比较原始的东西,它不喜欢去过分宣扬自己,去自己画的怎么怎么好,把东西怎么展现给人家。
华:就有一种园林的情结,就是造一个花园,自己在里面玩,玩的还很开心。
吴:对,还是有一种很安分的东西,自娱自乐的成分比较多。苏州现在画画好的人很多,但是苏州人我感觉画画可能受以前画风的影响,一个是苏州本身的一种气质,一种可能是地域性的东西,讲话的那种腔调、个性不张扬,所以画出来的画也带一点这方面的东西,像画国画的话就比较讲究细小的东西,比较讲究用笔用墨,用墨这方面你没有一种很大气的东西。
华:办企业跟创作教书育人这两个方面从感性上来讲,你更喜欢哪一个方面?
吴:从现在这个阶段来说,我倒反而更想静下来画点画,更喜欢创作。搞企业也搞了这么多年,真的是风险比较大。我已经搞了大概二十多年了,有时候吃的苦头也不少,也走过低谷。现在我那个企业总的来讲还不错,企业规模也一直逐步逐步在扩大,但是最近这几年,你们也知道金融风波特别对我们这种企业影响很大,因为我们是搞服饰行业的,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。从我个人的想法,企业最终我是要放弃的,最终的目的我还是要回到画画上来。在五十岁以后六十岁左右实际上是一个最好的阶段,特别我是又丢掉这么多年了,可能成熟要晚一点。或是我还要通过一段时间的磨练,可能要到六十岁以后才会真正呈现出我自己的,画画上面能达到自己的一种境界。
华:最后,我想就是说能不能用一句话对母校提一点建议,或者希望,或者批评,也是很宝贵的。对现在的母校的这种状况或者是办学的新的思路有没有什么建议?
吴:我去年也跟王院长他们讲过一个问题。我希望办学校就像我们做生意一样,超市的东西也要做,品牌的东西也要做的。这样的话通过精品跟超市两方面的融合,才能办出你学校的特色,精品的东西为你打造一个品牌的东西,打造你队伍的一个影响的东西,你做超市的东西就是多赚赚少赚赚,解决学生的分配、生路问题。
华:就是两个要搭配一下。
吴:精英的部分太少,反正现在也慢慢在办一个纯艺术的东西,那种东西实质上是影响今后学校的一个声誉问题。就像现在你光是解决学生的工作问题,但是要么以后出个企业家,你不可能出得了很纯的那种艺术家、名人、大画家,这一辈就会少一点。
华:原来我们美校其实最强的专业就是绘画专业。我离开这个学校去南艺读书,然后我回来的时候发现这个绘画专业好像断了大概有六七年,就断掉了不办了。那么这两年,我到了装艺系以后陆陆续续又开始要恢复,那我要来负责把这个东西重建起来。包括有一部分的文物鉴定、书画鉴定这一方面的课程,各方面好像确实是在往精英方面走,培养一部分人才。
吴:对,本来就是说到我这一辈就感觉要断代了,接下来的话绘画专业没有了,本身一个学校的精粹,一个精美部分就要慢慢灭掉了。
华:学校变成了一个以设计为主的学校,其实我们最好的传统就往往是绘画这一部分。
吴:苏州现在没一个这样的学校在培养这么多的绘画人才了,现在主要归类到中央美院、中国美院这一块了。但是我觉得苏州这个地方应该有这个条件去培养这方面的,假如这方面的人培养出来能像以前一样延续,像苏州六十年代出来这帮人,八九十年代出了这一帮人,我是希望以后还会这样,这个学校还会一代一代这样,只要这个学校存在还会有这样一代一代传承下去。
华:我们还想邀请你到时候来给我们代一部分的课,因为毕竟都是从绘画这个专业出来的,希望把那个老的传统带回来。
吴:可以的,我也很喜欢。这次代课,我看学生虽然说基础不是太好,有的是从来没有用过毛笔,但是我感觉学校已经在重视这方面的东西,那我感觉这是一个开始。哪怕你今年第一届可能没什么,但是第二、第三届。我是感觉从招生的源头上做一点点对学生专业上的考核。还有一个就是说贫富问题,还有一个对学生的家境条件,我感觉也要考虑。我教他们画画的话,我那个东西也写意的,你临摹的话他一张纸刚刚画了几笔感觉不行弄掉了,弄弄又那个了,一天你说要画掉多少纸,但是叫一些比较贫困的学生你怎么承受得了?承受不了这样的费用,因为画国画这个费用的确是蛮大的。
华:瞬间消耗的东西比较多。
吴:瞬间消耗的东西,笔墨纸砚,而且现在差的宣纸画不出效果还要去买好一点的宣纸,所以说这一次我来教书我带来两百张纸,我每人发给他八张,我说这个我送给你们的。那天王院长在我还跟他提出来,我说你把整个班级去了解一下,就是哪些是比较贫困的,对用纸已经比较累的,他们的笔墨纸砚我来提供,我可以做这方面的工作。我真的很希望这个学校以后能出一批,真的像徐惠泉,像刘懋善那一代的人,一代一代的,这样出一批那种人,不要断根。
日期:2008年10月23日
时间:下午14:30
地点:苏州工艺美院
采访:华彬
摄影:刘洁
摄像:黄新军
整理:徐彩萍
编辑:佘凌燕